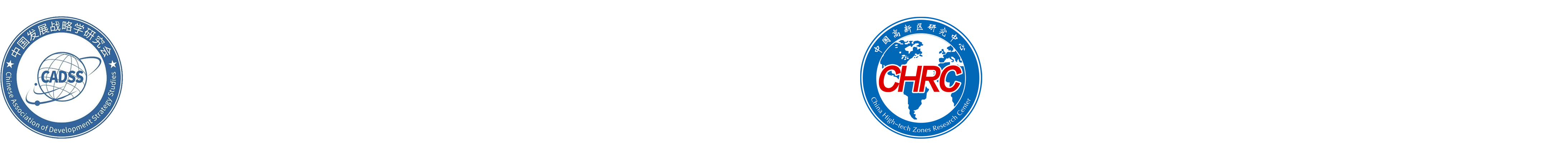新晋诺奖女得主的经历反映出科学界的重大顽疾
发布时间:2023-12-12 14:10:42 阅读量: 作者/来源: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2023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科学界重大事件在隆重的仪式中落下帷幕。但是,诺贝尔奖不仅带来人们对新的获奖人物、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新奇,更应对在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多重危机挑战下,科学创新还存在问题的反思!科学创新还需要反思?是的,诺贝尔奖往往让人们能够看够看到科学研究的一些顽疾。比如今年的医学生理学奖,女得主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的经历让人唏嘘。她曲折的科学研究经历,反映出科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科学界并不像社会想象的那样崇高伟岸,恰恰存在着对重大创新的文化与制度性压制!
卡里科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使得针对新冠大流行病的有效mRNA疫苗得以开发,为人类战胜实际疫情做出卓越贡献。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研人员,她的职业生涯却一直非常不顺利,其研究不受同事、同行和学校的认可,年薪从来没有超过6万美元,一直没得到一个正式的教职(曾短暂担任过a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八年申请不到基金。在学校的位置甚至被降级,后来不得不辞职,转向产业界去在疫情期间各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BioNTech公司。而且当时也被同事嘲笑:去了一家连网站都没有的小公司。
幸而,人类有了卡里科的坚持不懈,才在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更早地取得了胜利。新冠病毒来了,证明了卡里科研究的巨大价值,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和家庭。然而,试想下如果卡里科一直被打压无法成功呢?应对新冠病毒的局面又会怎样的糟糕?卡里科的经历不值得整个社会、不值得科学界对重大创新的遏制这种顽疾进行反思?予以改变、予以铲除吗?
卡里科的情况不是个案,在科学史上和现代科研中,遏制重大原始创新被打压的事情屡见不鲜,真正能够得到关注的都是坚持不懈的成功者,有多少重大的研究,被科学界这个有着发现真理、探索未知美称的共同体扼杀!科学界对重大原始创新的遏制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在自己的单位与同事中,一个科研工作者有一个特别新颖、与众不同的重大原始创新想法,因为这些想法与原来很不相同,往往会受到周边同事的抵制甚至反对。“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价值!”“这样的研究毫无意义!”诸如此类的话语是不是有些耳熟?卡里科的工作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说明,在科学界这样一直受打压得不到机会的人非常多,只有像卡里科这样少数的幸运者,有一天诺贝尔奖证明了她工作的价值,才能冲破压制得到世人认可。不过可悲的是这个证明用了600多万人死亡,整个人类跟着一起发烧、咳嗽,这样几乎每个人都有份的惨痛代价!
第二方面,重大原始创新的成果往往很难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因为重大原始创新往往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论,但是因为与主流的研究方向、方法不同,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同也相当困难。这样的事件不但许许多多的普通科研工作者经历过,很多诺贝尔奖的得主也同样不能幸免。
从远的讲,193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名鼎鼎的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对!就是物理学家说的“费米子”、还有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之问”(有兴趣者可以查下费米之问的内容)的贡献者,他的文章当年曾经被最著名的科学杂志Nature拒稿。再往近一点儿,罗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这位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她当年曾经给《临床调查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投稿,结果得到的回复是:“很抱歉我们不能接收您的文章。您的结论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较为武断。领域内专家强烈反对您的部分结论。他们认为您的对照数据不足,不足以证明您的观点。您的数据虽然有趣,但得出的结论却不能让人信服。”
再往近一点儿,诺贝尔奖得主得奖前的文章曾经被拒绝也是很多,比如,彼得·拉特克利夫(Peter Ratcliffe),这位201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他的文章1992年被Nature杂志退稿。
如果说被周围同事小范围的不理解不认可,是我们的周边同事视野眼界不够,可是科学共同体,尤其是科学界最高声誉的学术杂志,对于原始创新也以很多荒诞的理由轻易地拒绝,这是值得科学界反思的!科学界目前的学术成果发表制度,能够有效识别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吗?一方面现在科学界产生的文章非常之多,很多杂志的投稿量非常大。不要说Nature、Science这样世界顶级杂志的正刊录取率非常低,只有6%左右,就是一般国际SCI期刊的录用率平均也只有30%左右,而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在这样被大量拒稿的文章中,一定会有不少非常有原始创新想法,对于学科,对于行业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现在随着科学界发表文章的途径越来越狭窄,编辑会用一些自己的主观臆断,就轻易的拒稿。尤其比如像Nature、Science这样综合性的杂志,编辑的知识面未必很宽,对于一些重大的科学问题不一定有识别能力,仅仅是为了减少工作量,更是非常随意,没有深入的理由,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把80%左右稿件驳回,不进行同行评审。
另一方面,由于原始创新成果,尤其是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在基金申请和论文发表的同行评议中,同行学者对此并不了解,甚至不接受与原来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很容易不被接受。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顽疾,非常需要科学界改革(抱歉!具体办法需要群策群力)。不然的话,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被埋没、被扼杀。
第三,很多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会受到科学界权威的反对甚至打压。这里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案例,一个是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钱德拉塞卡是印度裔的美籍科学家,1953年他到英国牛津大学求学,他所提出来的理论与当时天体物理学的传统理论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他的研究恰恰受到了他的导师,非常著名的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勋爵的打压。
爱丁顿勋爵就是那位通过观测证明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是在人类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但是恰恰是这样科学界的极其有威望的权威,却对自己学生的理论不但予以反对,甚至在学术会议上撕毁了学生的文章,当着全体会议人员的面羞辱这位提出新观点的学生。钱德拉塞卡在1953年就提出了重大创新的理论,可是一直未受到科学界的认可,50年后才获得诺贝尔奖!半个世纪呀,人类要等到这么久才能对一个重大发现予以承认,时间不是太长了吗?
另一个例子就是科学界的巨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后来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他其中还用到了洛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这个变换是1902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得主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tz)提出的。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没有得到洛伦兹的支持,他一直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观点。好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较快得到了验证。但是即令如此,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时,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不敢对他在相对论方面的成果予以确认,是把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作为他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讽刺。
因此,综上所述,科学界对于重大原始创新一直有着阻碍、不认可,甚至由于人性的丑陋故意的打压。科学界被号称是最具创新性的群体,但是历史和现实充分的说明,科学界内部还有着非常强烈的因循守旧倾向,对创新,对于创新成果,尤其是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存在抵制反对的环境和氛围。
从16世纪末,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de Galilei)奠定了实验科学,从1642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奠定了经典力学,开创了人类的科学研究之先河,人类的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历史也有400多年了。这400多年间,上述遏制重大创新科研的案例是非常多的。但是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人类正在面临联合国说的三重危机(Triple planetary crisis):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以及贫困、疾病等多方面的挑战,特别需要我们现在有重大原始创新,才能应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危机。国际能源署(IEA)的评估表明,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确定的控制1.5°C度或者2°C温升目标,因此也特别需要科学界、技术界的原始创新来为人类找到走出困境的途径。
然而,科学界一直存在这样的因循守旧、遏制创新的文化与制度,如果不改变,人类怎能应对21世纪面对的重重挑战?难道我们还需要下一场危机?像新冠疫情这样的下一场危机?我们才能证明一个新的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吗?如果像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预言的,人类每20年就会发生一场大流行病。而恰恰下一次大流行病发生时,我们不再幸运的有人像卡里科这样为新疫苗研发奠定了科学基础的成果,人类能够应对的了下一次大的流行病危机吗?